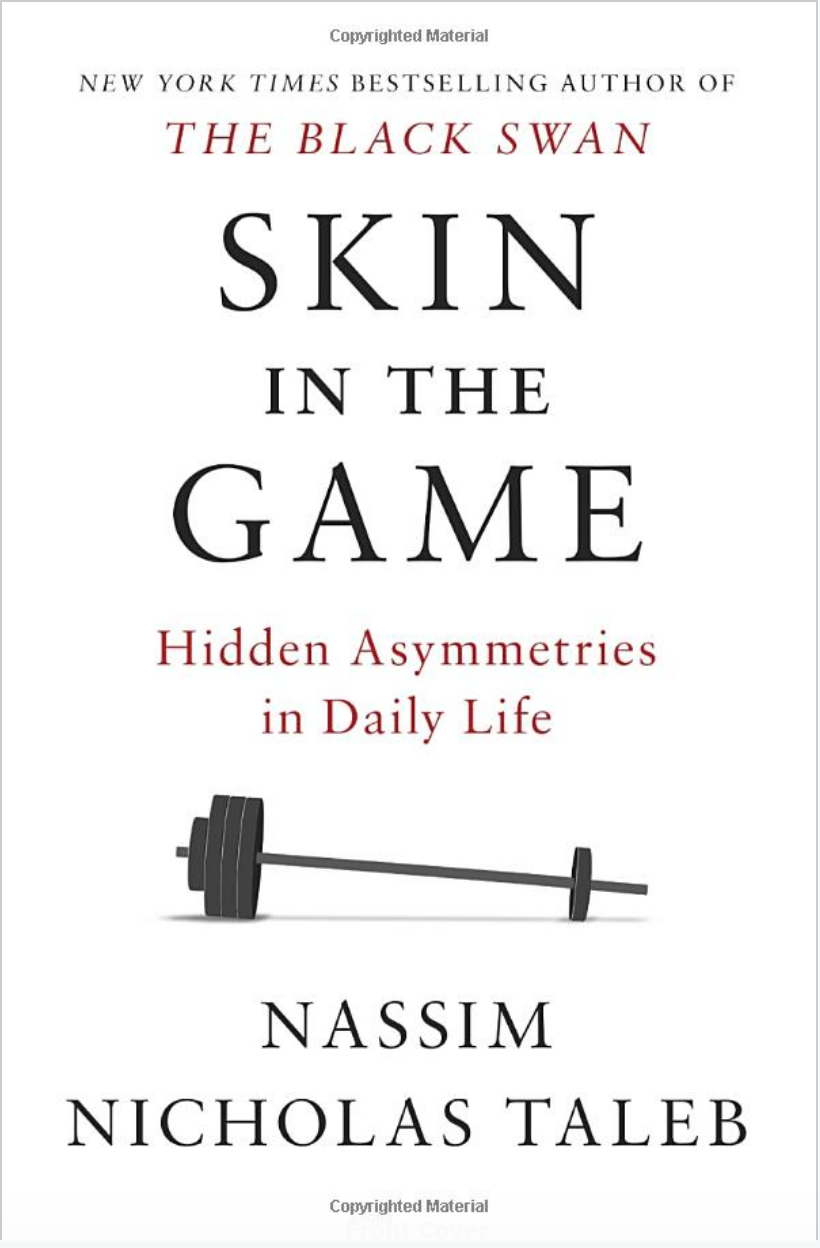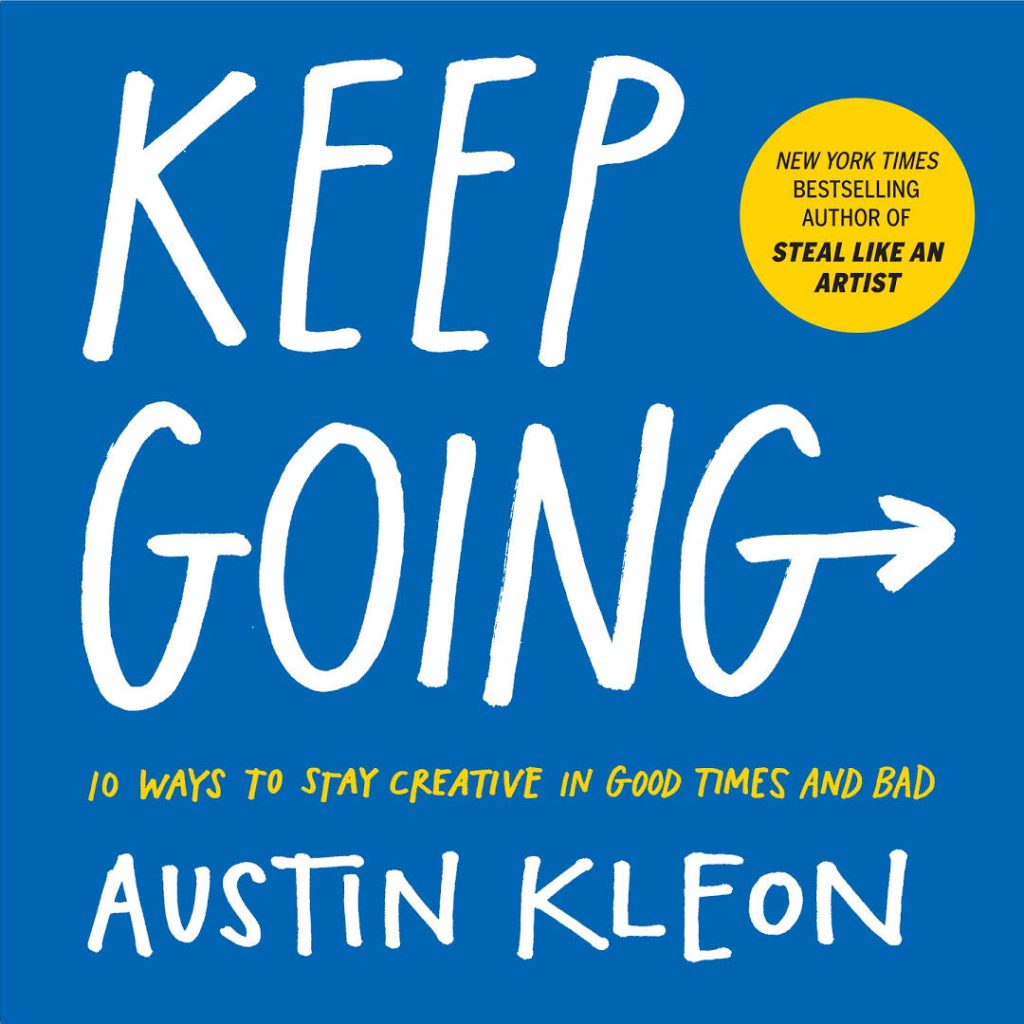不久前我到港大參加一個創業的活動,事後一位在外資銀行工作的朋友趨前打招呼:嗨,我看過你的文章,你曾說過「出類拔萃者,不著相」…
我略顯驚訝,那是三年前寫的一段文字,想不到有人印像深刻。文字引用自當時看的一本書,提到各行各業最頂尖的人,都「看起來不像」那種人,因其行事作風與眾不同,反而另闢天地,成就出人意表。
巧合的是,我最近在看《黑天鵝》作者 Nassim Nicholas Taleb的新書Skin of the Game時,他恰恰也用了一整個章節(第九章)來講這個道理,非常精采。
Taleb看不起主流社會所推祟的精英階級或「成功人士」:企業高層、政府官僚、知名學者等,認為他們脫離現實,毫無真本事,卻盡享社會賦予他們的好處,不付出代價;相反,Taleb尊敬那些靠自己技能努力打拼的人,像創業者、理髮師、甚至街頭賣藝人,認為他們憑一技之長自給自足,是有skin of the game(切身利害)的人,比前述的特權階級更高尚。
那出類拔萃者為什麼會看起來不像同類?Taleb認為,因為有真材實料的人,不會隨波逐流,也不靠外表去爭取同儕認同。他舉例說,若自己需要進行手術,有兩位同等資歷的醫生可以選擇,一位外型如「程志美醫生」,另一位看來像個屠夫,他會毫不猶疑取「屠夫」而棄「程志美」。原因是「屠夫」以如此格格不入的「造型」而獲得和「程志美」同等的地位,等於當事人刻意「輸在起跑線」,並曾突破重重障礙,那他非具備超凡的才能不可*。
Taleb進一步解釋,對某些職位來說,例如大企業高管,一個人擁有良好的形像和履歷,比其具備真材實料重要,所以他們看起來幾乎千人一面,連用詞也幾乎一致(回想一下你在電視新聞中見過的政府高官,或大機構發言人)。但最出類拔萃的那1%、甚至0.1%者卻不同,他們毋須靠履歷或形像行走江湖,所以不著相。
回想我近來遇上一位最有潛質的創業者,是個中學讀了七間學校、兩次唸大學都無法完成學業的所謂「廢青」。類似例子還有不少:Steve Jobs未成功之前,是個吸食迷幻藥、行事乖張的異類;馬雲是個英文教師;而一些看來很「啱數」的,如Theranos的Elizabeth Holmes,卻證實是個騙局。我一位當交易員的朋友曾誇張地形容,他們那行實力比造型重要,只要能賺錢,「著條底褲返工都得」。還想起一個不甚恰當的比喻,在神劇《Breaking Bad》中當「大毒梟」的Heisenberg,真實身份是個懼內又患上絕症的化學老師。真人不露相。
當然,若為顯得「出類拔萃」而刻意追求「不著相」,就是本末倒置了。
*Taleb原文解釋得很好,我直接引用好了:
“Simply the one who doesn’t look the part, conditional on having made a (sort of) successful career in his profession, had to have much to overcome in terms of perception. And if we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people who do not look the part, it is thanks to the presence of some skin in the game, the contact with reality that filters out incompetence, as reality is blind to looks.
When results come from dealing directly with reality rather than through agency of commentators, image matters less, even if it correlates to skills. But image matters quite a bit when there is hierarchy and standardized “job evaluation”.”
***
本文同日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