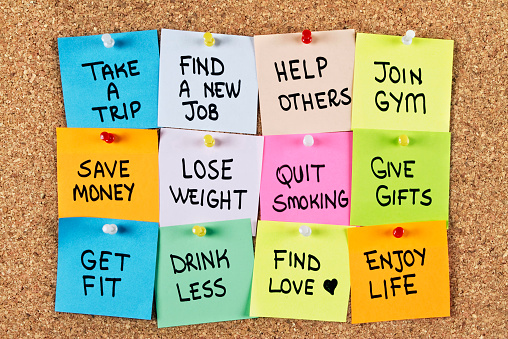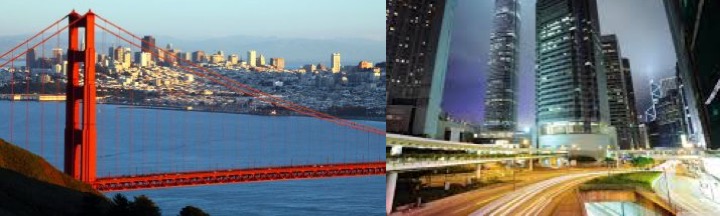最近一年半載,創業圈子裏朋友們聚首的主要話題,並不是什麼最新的人工智能或區塊鏈技術,而是去留問題:留在香港,抑或去其他地方碰機會?
有個創業的朋友,三十出頭,女友也在自己的初創工作。他說在這段時間,她一有機會就往新加坡跑,一方面參加當地形形色色的創業活動、多結交朋友,另一方面也在發掘有沒有留在當地發展的機會,孜孜不倦。
這女孩的行為毫不特殊。看身邊有意離開的朋友們,本身從美加回流的,選擇比較明顯;土生土長的,很多在想台灣,或者新加坡,甚至泰國。回國發展事業的人當然不少,北京、上海、深圳等,但沒哪個表示有意回國安家,原因不言而喻。
我默默觀察朋友們的言行,間中為舉家移民的朋友餞行,但很少參與討論,因為一提起就頗感傷。明明主旋律是國家要大力發展大灣區、催谷創科經濟,有本事的香港年輕人應該感到前途一片光明才對,為什麼反而想逃離?又,這些人離開了,哪些人想擠進來?當我懷著這些疑惑嘗試找答案時,卻赫然發現,遠在彼岸的美國加州灣區,情況竟與我們出奇地相似。
最近在Medium上看到一位灣區女孩的自白,如果捂住其中的地名,內容和香港年輕人的心聲幾無二致:
這位叫Diana的女孩正送別一位兒時好友Eleanor往機場,對方打算離開三藩市前往匹茲堡定居。她們二人從一起長大,關係親厚。Diana在初創公司工作,薪金和前景都不錯;Eleanor的興趣在文創方面,過去一段日子過得很不遂心。她原來的住處在2016年一場暴雨引發的水災後已無法居住,不得已搬回去與父母同住,卻沒料到兒時居住的小社區已成為新晉遊客區,搬進不少富人。Eleanor在小店工作,向遊客們售賣標價過高的商品,薪水不多,既無法負擔租金自己一個人住,又感到從小長大的社區已人面全非,毫無親切感。眼見已搬離灣區的朋友們,一一在生活成本較低的城市立足,故萌生離巢之意。
Diana送別Eleanor時在心中默數,過去兩年來,這已是她第12位離開灣區的朋友了。她的一技之長使她成為近十餘年來,科技企業在灣區發展起來的既得利益者,但朋友們卻沒那麼幸運。Diana不禁反省:是不是因為我們拉高了灣區的生活指數,令這些科技行業以外的朋友成為輸家,無法在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立足?
如果參考一些較宏觀的經濟數據,發現結論與Diana的切身經驗十分脗合,加州的面貌每年都在緩慢地變更中。年初加州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發表了一份橫跨十年(2007至2016年)的移民數據,有幾點值得一提:
- 十年間共有600萬人離開加州,500萬人移居進來;加州的淨人口流出為100萬人。
- 大部份加州人移民去生活指數較低的州份,如:德州、阿利桑那州、內華達州、俄勒岡州等;而移居到加州來的,以紐約、伊利諾州和新澤西州的為主。
- 大部份離開加州的是低收入者(年收入5.5萬美元),而新遷居進來的則以高收入者為多(年薪20萬美元以上)。
- 有家室的、教育程度高中左右的加州人不少舉家移民到上述生活指數較低的州份;而流入人口則以26-35歲、大學至碩士程度的紐約、新澤西州人為主。因此加州整體社會越來越顯得富裕、中產。
簡而言之,和古今中外所有大都會一樣,加州越來越成功,也越來越「不易居」。一個漸趨「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社會,很難擺脫居民收入差距加劇、貧富更加懸殊、本土與仇外情緒等等一系列問題。這情況在最發達的灣區尤為明顯。
年輕人如果並非從事吃香的科技行業、或者靠父幹(「沒什麼,爸讓我打理一個風投玩玩」),不要說「上車難」,連賺取稍為可觀的薪水都不容易。另一個統計數據顯示,從1997到2017年的20年間,除最高收入的百分之十外,所有矽谷上班族的月薪經調整通脹後,都比20年前的低。收入位處中游的上班族受創最深,整體收入比20年前的低了14.2%。這情況在美國其他地區都沒發生,全國收入最低者過去20年薪水仍有輕微增幅,但矽谷的收入差距卻在惡化中。
土生土長的灣區年輕人,一方面送別意興闌珊的朋友們, 另一方面迎來趾高氣昂的「新灣區人」,看見自己從小長大的社區變得名店林立,感受科技霸權左右政府政策,加上苦無上車機會…這種怨氣,香港年輕人一定毫不陌生。
幸好在彼邦,「覺醒」的不止年輕人,還有一些發財立品的科技新貴。例如Salesforce的聯席CEO及主席Marc Benioff便發願,樂意負擔更高的企業稅款,好助三藩市市政府籌足三億元,幫助區內流浪漢(因為上車難、租金上漲,三藩市的露宿者問題幾為全國之冠),甚至不惜為此與持相反意見的行家(如Twitter的創辦人Jack Dorsey)公開罵戰。
從來頂尖的大都會都是「圍城」,裏面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離開的人已離開,留下的人,可會為這城做些什麼?
相關舊文:
矽谷巨富的恐懼
獨角獸又如何
參考資料:
Marc Benioff voiced concerns on a San Francisco homelessness measure months before becoming its most prominent booster
Inequality in Silicon Valley is getting worse: Wages are down for everyone but the top 10 percent
Leaving California: Here’s who’s moving in, who’s moving out
Californians fed up with housing costs and taxes are fleeing state in big numbers
If San Francisco Is So Great, Why Is Everyone I Love Leaving?
***
本文11月23日及30日分上下兩期,刊登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