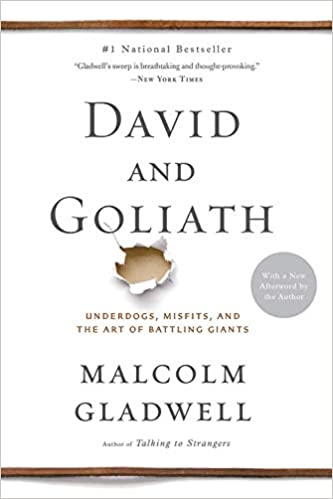有商業機構針對英國的「Z世代」(大約在1990年代末至2010年前出生者)進行了一項調查,了解他們對工作的看法。調查發現,這些廿多歲的上班族不喜歡工作地點離住家太遠,最好能在家工作;他們重視薪酬和晉升機會,此乃他們是否接受一份新工作,或是否辭職不幹的關鍵;僅次於「升職加薪」的條件是工作意義,他們盼望工作有滿足感,不致無聊重覆。
(相關舊文:千禧上班族)
簡而言之,Z世代的理想工作不但收入要好,而且上班形式還要靈活具彈性,最好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世上是否有這樣的「筍工」,能同時滿足一名打工仔的自由、收入與熱情?我只想到一種:自己做老闆。像我剛剛認識的一位女生Alexandra,似乎正是這樣一位找到「筍工」的Z世代。
Alexandra才廿六歲,大學就讀傳理系,四年大學生涯裏,她四年都在兼職做「小編」,「我喜歡餐飲業,所以毛遂自薦到不同的餐廳,為他們管理社交平台。」年紀輕輕已一身豐富經驗。
畢業後她順理成章到一家走中高檔路線的餐飲集團任職數碼營銷,包辦拍照、拍片、定期為餐廳發帖文,時為2019年,工作才上手就迎來最終蔓延整整三年的疫症。
2020年年初,公司眼見堂食生意快「清零」,轉型催谷外賣,對年輕的Alexandra委以重任,由她為公司編寫全新的外賣落單網頁,「公司說如果外賣生意好,就不必炒掉前線員工。」結果她把外賣平台趕出來後,公司生意果然好轉,但還是炒掉不少員工。那時Alexandra開始萌生去意,覺得即使做好份內事,還是無法左右公司的決定。她想自己當老闆。
2020年5月,疫情下餐飲業開始漫長的寒冬,Alexandra卻選擇在此刻離職創業,和來自倫敦的男朋友合夥開設公司,專為餐廳經營社交平台、網上營銷。我以為自己聽錯,這麼差的環境下,哪有餐廳還有預算搞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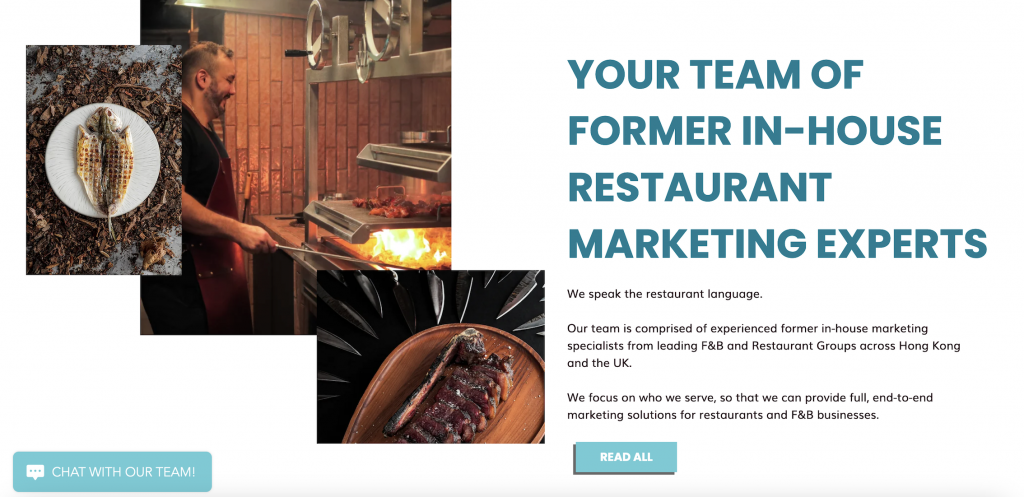
我到底是外行人,Alexandra的生意正是因為餐廳緊縮開支、撤掉原來負責營銷的員工而來!因為他們以外判商的身份,「成為餐廳的in-house營銷人員」,Alexandra向我解釋道。她公司向餐廳收取月費,定期在其社交平台發出一定數量的帖文,形式包括相片和短片等,以保持餐廳的人氣,吸引客戶光顧(疫情嚴峻時催谷外賣,好轉後也推銷堂食)。餐廳只須付出全職員工一半甚至三分一的月薪,就可獲得差不多的網上宣傳效果,自然樂意與Alexandra合作。
對Alexandra而言,她對經營社交平台的流程早已滾瓜爛熟,對各種吸引目光的技巧亦了然於胸,加上為餐飲集團工作時已和攝影師、設計師等合作無間,所以在接下生意後,很懂得將之有系統地分拆成小項目,讓不同崗位的同事協作完成。她的營銷公司在餐飲業的冰河時期成立,生意卻一年比一年好,現聘用十來人、有卅多個客戶,一年的營銷額達數百萬元。一位廿多歲的年輕人能有這樣的賺錢能力,真不簡單。Alexandra笑說,她家裏個個都喜歡做生意不愛打工,媽媽有家美容院、哥哥開了四間地產舖等,他們都是她的榜樣。
從Alexandra身上我看到一種Z世代工作的新方向。她本人固然脫離上班一族,成為自僱者、生意人,那些和她合作的公司,也省卻管理Z世代的負擔。前面提到Z世代又想工作靈活有彈性,又想做自己喜愛的事,一般日復日的辦公室生涯無法滿足他們,管理他們的上司也常感到沮喪。「握緊拳頭,裡頭什麼也沒有;打開雙手,你擁有的是一切」,與其扭盡六壬搶人、留人,也許可試試放手,順勢把部份工作外判出去,由喜歡彈性工作的Z世代承包完成。也許這種合作形式,更適合企業需要,也更符合Z世代的本質。
***
本文分上下兩集,於上周五及今日見刊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