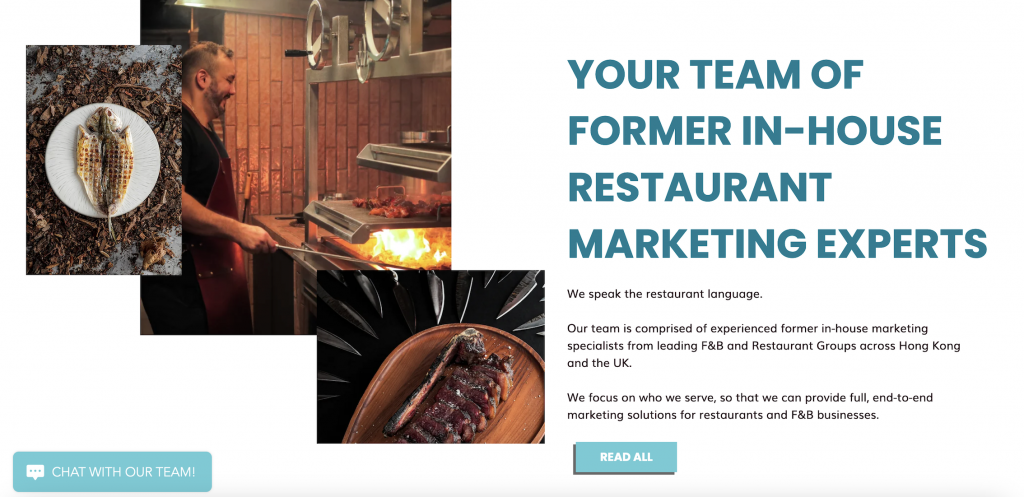上次提到經濟雖然復常,但市道似乎未見強勁反彈,我所熟悉的初創圈子,深受疫情和加息雙重打擊的企業並不少。一位CEO向我提起,他在辦公時間,幾次見到另一位初創創辦人在數碼港附近跑步,對方幾個月前蝕讓自己的公司後,似乎仍在待業中;另一位則說,美國科技界的情況比香港的更糟糕,許多巨企毫不留情地大幅裁員,他有不少朋友在科技公司最風光時入職,享受高薪和優厚福利多年,突然失業,很難適應。
(相關舊文:市道差不差?)
大型科技企業裁員的消息,自去年開始不斷傳出:Google、Meta(Facebook)、Twitter等,無一倖免。矽谷去年的裁員人數高達363,000,今年大離職潮仍然持續。三年疫情本來令很多科技公司業績異常出色,但持續加息卻對科技公司特別不利。有負債的百上加斤、需要融資的根本得不到投資者青睞(投資極低風險的美國國債已有不錯的利息回報,高風險初創怎不令人卻步),它們面對經營成本高漲,不得不厲行裁員節流。
裁員對勞資雙方都是艱難的事,但大家面對的後果卻頗不一樣,尤其是科技界。對企業而言,瘦身後有幾個明顯好處。其一是架構和流程更精簡,行政上的架床疊屋大減,營運效率明顯得以提升;其二是可專注於有盈利的業務,和有潛質的產品開發,尤其後者,往往成為它們反敗為勝的關鍵;其三是可投放更多資源在留下來的員工身上,例如加強培訓、提供更多晉升機會、增加福利等,令他們工作起來更有幹勁。
不少科技公司都曾利用裁員瘦身的機會,扭轉形勢,矽谷其中一個最為人稱道的例子是Netflix。時為科網泡沫爆破後的2001年,剛成立三年的Netflix面臨首個存亡危機,忍痛裁員三分一止血。出乎意料的是,精簡後公司沒有因為人手不足而影響表現,留下來的同事反而工作得更有活力和效率,令其CEO Reed Hastings領悟出「人才密度」(talent intensity)的道理,認為篩走表現欠佳的冗員後,有能力的同事反而工作得更得心應手。
(相關舊文:Netflix裁員 士氣反升?)
這當然是老闆的一面之詞。那些因為裁員而失去工作的人,面對的情況肯定完全不同。這次科技界大離職潮中有不少資深員工被裁,他們職業生涯的大部份時間都效力於薪酬、福利好得離譜的科技公司,一下子失去工作、地位和收入來源,滋味真是不足為人道。
首先要面對的轉變,是要接受比原來低得多的收入,否則可能長期待業,或需打零工幫補生計。單是要過這關已非常困難,因為不少人有房貸、孩子學費等固定開支,不能說減就減。
有人認為不如利用這機會創業,反正已長期浸淫在科技界,有能力、有人脈、懂市場,可放手一搏。成功例子有Airbnb的幾位創辦人,他們本來都任職初創,卻因為2008年的金融海嘯而「被創業」,破釜沉舟下,想到出租客廳給旅客的主意,如今總算名成利就。
但正如大前研一所說,被大公司「馴養」太久的僱員,很難成功創業,因為改變心態太難。一直在大集團工作的行政人員,是習慣凡事按部就章的「正規軍」,不管做什麼,先分不同部門跟進,但初創根本沒可能有這麼多人手供使喚;更重要的是,向來薪高糧準的行政人員通常不敢冒險,亦稍欠「使命必達」的企業家精神,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安身立命非常困難。Airbnb的幾位創辦人,「被創業」時相對年輕,受僱時間短,要轉型比較容易。像他們般成功的例子極少。
大離職潮下,「世上再無鐵飯碗」的情況更形明顯,即使有份好工的,也要培養「反脆弱」的心態,才能應付日趨動盪的環境。
(相關舊文:世上再無鐵飯碗、為什麼揸的士好過打工?)
***
本文分上下兩篇,分別見刊於上周五及今日《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