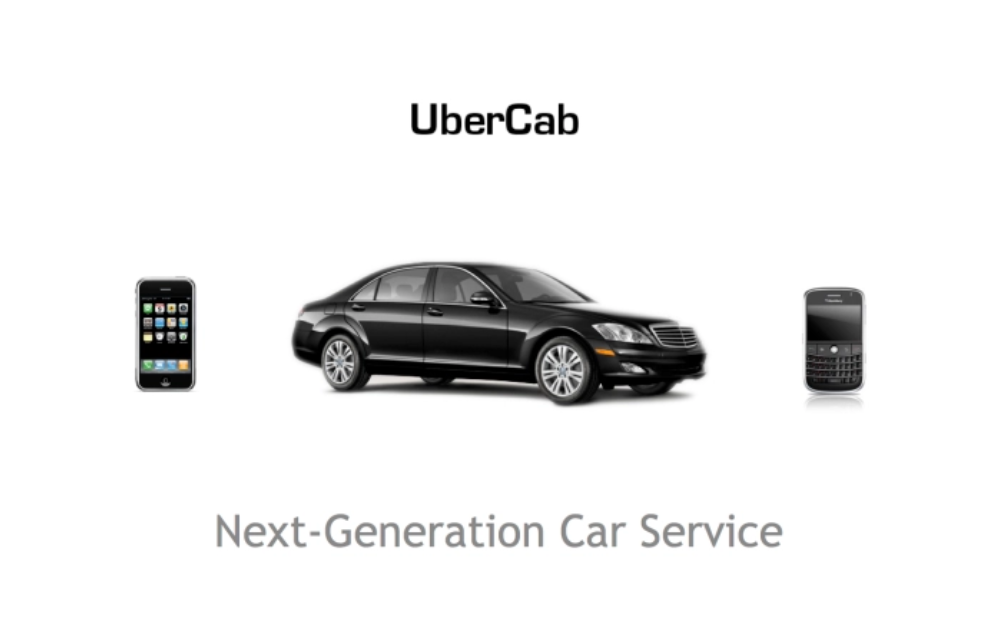和一位在美國、內地和香港都有投資經驗的風投聊天,她提到一個香港獨有的現像,就是「創業團隊交上來的PPT(融資簡報)實在做得太漂亮了!」
這話並無貶義,只是點出一個奇特的觀察:誰都知道三地之中,以香港的創投氣氛最弱、融資市場最小,創業沒做出斐然成績來,但做PPT的水準卻堪稱「世界第一」,何解?
我身處香港創投圈子太久,對此現像早就麻木,經她一說,頗有共鳴;而且我也很快想到其中一個原因:因為香港的專業投資者太多、有科技創業經驗的投資者太少。
任何一個創投風氣濃厚的大城市,都有三個主要特徵:(一)巨型科技企業林立(二)大量風投設點和(三)科技人才聚集。資金、人才、土壤,三者俱備下,不但產生相當濃厚的創投氛圍,還孕育出一種特殊的投資者來:有創業經驗的投資者,尤其是天使投資者,表表者包括Peter Thiel、Marc Andreessen等大神級人物。
這類投資者因為一次或多次成功的創業及退場(exit)經驗,不但累積了創業的經驗和人脈,也得到相當可觀的金錢回報。人生到了一個階段,他們或許沒有動力或精力再創業(所以永不言休的Elon Musk廣受愛載,因為他本來可以退休享受人生,而選擇繼續拼搏),但創業家精神亦在,加上有一輩子花不完的錢,令他們有充沛的資源和意願參與最新的項目。天使投資者這種角色,可謂完全為他們度身訂造,讓他們可以繼續發光發熱,指點江山。而對年輕的團隊而言,前輩有的不只是錢,還有創業者最需要的智慧、經驗和人脈,兩者可謂一拍即合。
(相關舊文:雅虎香港幫)
專業投資者未必有創業經驗,他們的專長是看分析、數據、報告;如果來融資的團隊和恰巧和他們一樣,擁有亮麗的學歷、翩翩的風度和流利的口才,加上一份設計得一絲不苟的精美融資PPT,比較容易得到這些專業投資者的垂青。
但前述擁有創業經驗的投資者則不一樣。他們是熬過創業的苦的,深深體會話講得再天花亂墜,都不及直接動手解決問題來得實際。學歷、履歷、外型、口才、講英文冇港式口音等…不是不重要,但遠不及執行力和不怕蝕底的精神更重要。用一張畫了草圖的餐廳面巾,換一份知名風投的term sheet,這類傳奇幾乎只會發生在鍥而不捨的團隊和有創業經驗的投資者身上。美侖美奐的PPT,似乎對這類投資者作用有限。
剛才提到那位有三地投資經驗的投資者說,她看過Uber第一份融資的簡報,只有十來頁,而且畫的還是火柴人,卻成功打動了一些識貨的投資人,開創出一個數百億美元的江山。我在網上搜過,找到的版本有25頁、沒有火柴人,但設計卻也談不上精美(這裏引用的圖片,就是它的首頁):
Here is Uber’s first pitch deck
我擔保香港任何一支數碼港或科學園的創業團隊,都能做出比它精緻得多的融資簡報來。漂亮的簡報更能討專業投資者歡心。
香港不乏身家豐厚的創業家。《福布斯》榜上的香港富豪,很多都是白手興家的,但上一代的富豪多數靠地產發達,對科網團隊未必感興趣,也很少成為他們的天使投資者。剛才提到一個創投氣氛濃厚的大城市,都有三大特徵:資金、人才、土壤,可惜香港在這三方面都有所不足。或許要等香港出現一大批靠科網起家的投資者後,才能改變整個創投的氛圍吧。
附:Guy Kawasaki’s 10/20/30 Rule of PowerPoint
***
本文精簡版率先於《晴報》專欄「創業群俠傳」見報